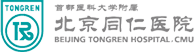magazines
当我放慢脚步
那天又没有按预想的时间冲向回家的路,急诊手术下的就晚了,之后又忍不住上楼去听讲课。如今科学发展的那么日新月异,几个月的产假休完,我那近乎水肿的大脑好像急需充电。
六七点种的地铁里,人还正多。没有晚报相陪的路上,多少有些无聊。想起书包里有几本同事送给我儿子的小布书,当众拿出来看确有些可笑,没关系,我不用预习,回家照样给他娓娓道来。正准备给我那每晚必打开手机看短信的老爸发信息,已经到了建国门换乘站。走过环线换一线的下行台阶,我再一次对人群拥杂在狭窄空间的场景产生了紧张情绪。如果现在发生新闻中偶有播报的灾难性事件,难道我也要踩着前人的头颅杀出一条生路?算了算了,我不希望这是白天工作紧张带来的恐怖幻想后遗症。
一线的站台相对宽阔些,人们的步伐也明显加快,为了尽量避免与拥挤一路同行,我也习惯性的匆匆向前。不经意的,我发现站台中间有个身影的相对速度和我相差挺大,当我到他旁边,下意识的瞥见原来是一个踌躇的老人。我能感觉到他是冲着往东去的地铁走,只是挪动的太慢了。从他身上能看出曾得过脑血管病的痕迹,因为已经明显到连那副方框眼镜都只能歪戴在脸上。这种判断清晰起来的时候,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隔着大约十几米的人流,我发现他从站台中间往上车方向也就前进了一两步而已,似乎还扶靠在一旁的台柱上。我该…? ?顾不上想那么多,因为我已经听到了地铁开过来的声音。“您要去哪儿啊?”我快速走上前去问道。“这,这是奔四惠去的吗?”这是一张苍白的面孔。“是啊,来,我扶您上车吧。”这时,我才发现他的确需要多一双手的支撑,我们趁车门关上之前上了车。列车的启动显然使老人的不便更引人注意,挨车门座位上的两个人不约而同站起身,请老人坐下。我也没顾上象平时那样低头往里钻,四处捕捉座位,只是随便站在车门旁,内心却有了一种满足感,这种感觉,相信不比成功完成一台鼻腔泪囊吻合术差。也许,当困难真正被发现的时候,善良还是无处不在的。只是,我们大家都太忙了,忙得让身边很多事情都变的那么匆忙而没有意义,忙得只能让视野变窄。当我们放下那颗急躁而焦虑的心时,会不会换来内心的平和与充实呢?
“大望路到了”那位老人赶忙费力地站起身来,“您不是要到四惠吗?还有一站,下一站才是。”站在车门旁的我扶住了他。“噢,好,好”他又坐了下去,抬头看着我,“你没走啊?”我随意地点了点头。“我,我没别的意思。你,你贵姓啊?”这到让平时常听病人这样问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了,只有以笑做答。“你贵姓啊?谢谢你,谢谢你在我危难的时候帮了我。”“危难”,危难肯定谈不上吧,殊不知,我整天的工作才是救人于危难呢。我这样想着,已经到了四惠站,我扶他到了车门,他自己下了车。我并不为没有送他到目的地而不安,因为我相信:在如潮的归客中,一定还会有一个愿意放慢脚步的人走上前……